【编者按】
公元前4000多年,半坡先民在建房时埋入粗陶罐和人头骨,以祭土木、魇风水;公元前91年,朝野起“巫蛊之祸”,长安大乱、万人殒命、太子被逼自杀;1995年,世外桃源的泸沽湖,被认“有蛊”的若玛一家世代被村人孤立,母亲葬礼村中无一人到场;2017年,广州纯阳观门前专辟空地,供香客“打小人”“做法事”;2024年,昆明邮局海关查获一批用人体组织制作的制品,走私者报称为“护身符”……
巫蛊是什么?为什么巫蛊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仍广泛存在?人类学家邓启耀,三十余年来致力于中国巫蛊现象与文化的研究,爬梳历史文字、寻访巫蛊实例,甚至亲身“试蛊”。在《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一书中作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等多方面梳理了“巫蛊”这种非常态的精神状态和群体迷乱,以及其背后潜藏的深层次问题。本文摘编自该书绪论部分,澎湃新闻经北京贝贝特授权发布。
对于一个置身于21世纪现代科学文明情境中的读者来说,本书所谈论的事是极为荒诞无稽的。然而,问题在于: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真正生活在这样的“情境”之中?
翻开中国历史,满篇皆是权争、宫斗、战争、灾祸。然而,这不过是可见的浪潮。在汹涌波涛之下,一股潜流往往被忽视。它讳为人谈,却深潜于人心暗黑之处,伏窜于宫闱与茅舍。它会是弱者自保的密咒,俗众伤人的流言,也会是权贵争权的暗器。一旦和权力、利益挂钩,或者仅仅出于羡慕嫉妒恨,潜流都可能喷涌而出,成为淹没他人的祸水,甚至成为影响历史的洪流。
古代的情况我们暂且不论,就说当代,是否人人都生活在纪年所标示的这个时代情境中了呢?我不敢断言,至少在我调查过很多边远山区和农村后不敢这样断言;甚至在我们生活的所谓“现代都市”里,新潮建筑或新潮时装包装里的人,是否真像他们身系的商标那么“摩登”呢?依然非常可疑。电脑算命、“科学”求签、对带“8”字车牌、电话号码及开张日期的迷信等等,难道不是巫术心理使然么?至于在人的名字上打叉叉或倒置以求“打倒”,在银行门口摆狮子以“吃”他人宅气财运而使自己大发,更是一种标准的巫蛊行为——哪怕它用的是现代名词和现代时髦包装。
巫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文化事象,影响深远而广泛,却又总是讳为人谈。远古的甲骨文卦爻或易象卜筮典籍里,涉及与社稷政事、王室安危相关的重大灾异病象,每每提到“蛊”这个字;汉代因宫廷权力之争而引发的“巫蛊之祸”,数万人死于非命,世人闻之色变,如同一次社会性的瘟疫;延至20世纪,至少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少人受害于巫蛊事件,人们至今仍像害怕麻风病一样地害怕“蛊”。甚至到了21世纪,种种巫蛊或准巫蛊行为仍然以不同面目出现。“蛊疾”,成为一种很难诊治、很难定义的病象,一种在巫和医之间纠缠不清的文化性或精神性的可怕瘟疫,而且,在民间,无论是放蛊、染蛊,还是治蛊、克蛊,都存在着一种沿袭了千百年的运行机制,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包含社会组织、制度、观念、符号、行为、器物等层面的神秘文化系统。如果说,“巫蛊”整个都是一种无稽之谈,那么,一个这样的问题也许马上就会随之而来:既然“巫蛊”纯属子虚乌有,为什么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有关于“巫蛊”事件的历史记录,以及十分现实的影响、十分具体的存在呢?
有关“巫蛊”的各类案例,我将在本书中加以详细论述。作为一篇绪论,拟按人类学惯例,先进入生活现场,对巫蛊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性精神性病理现象的文化处境和心理处境,开始田野考察。1995年和1996年两年春节前后,我和做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妻子都是在怒江峡谷中度过的。这是世界上数得出的大峡谷之一,山峰和谷底高差很大,坡极陡,攀援尚且不易,何况在里面过日子。然而,正是在这个石多土少的“V”形峡谷中,怒族、傈僳族等民族已经生息了很多世代,不仅在石头缝里生存下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我们的调查主要侧重在精神文化方面。由于和怒族、傈僳族掌握传统文化的巫师、祭司和群众交上了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帮助,我们才能够深入到他们心灵世界中,看到传统文化作用下,他们当下的文化或精神的处境。
在对一位怒族老祭司的调查中,我们详细记录了他表演的几个祭祀活动。这些祭仪,分别针对关节疼、心口疼、肚痛、中了巫蛊毒咒甚至做了噩梦的病人而举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病症,他都是用传统的“精神治疗”——祭鬼,来一一克之。这位老祭司认为,人之生病,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天象物候对人所起的不良作用,更重要的是某种精神性的邪气异灵与人相“冲撞”了。这种邪气异灵,既可来自自然界或超自然界,也可是人为作用。来自自然界的叫神鬼,来自人的叫巫蛊。
出于对陌生人的警惕,怒江一些民族对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人有多个层级的称呼形式,如傈僳族把河头(上游)方向的傈僳叫成“怒扒”,把河尾(下游)方向的叫成“楞梅扒”,把自己叫成“傈僳扒”。不论是“怒扒”还是“楞梅扒”,均有“看不起”的意味。这种评价类似王明珂在岷江流域看到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认知,羌族以流域位置区分“蛮子”“汉老子”“蛮娘汉老子”等。他们认为,“根根不好的那家”,便是指有蛮子与汉人的根根、有麻风病根根,或有“毒药猫”根根的家庭。这是他们区分“内外”的一种方式。所以,对于外来人,人们都会很警惕。怒族认为,如果家里有客人来过,家人正巧肚子疼或心口疼,便是客人的魂灵嫉妒主人而作祟、“放鬼”,这就要祭“心疼鬼”。祭师端碗冷饭,恶毒地咒道:“不知害臊的乌龟婆,不懂羞耻的母猪脸,乱咬人家的肚子,乱翻人家的肠子,呸……”把所有的脏话和诅咒说完,同时把冷饭狠狠泼洒出去,以此驱赶“心疼鬼”。
尽管我对这类说法和做法并不感到陌生,但使我吃惊的是,当地群众乃至不少地方官员,对这类说法的确信程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很多人向我们一一指证在大峡谷的山崖和箐沟深处隐匿的精灵,举出不少实例。例如,他们反复告诫我们,在村北有一个阴森的箐沟,在太阳照进去之前,人千万不能进去,否则会撞上邪灵,神经失常。他们提起好几个人的名字,说他们就是没弄对时辰进箐沟疯掉了。他们还说,箐沟两侧的山崖有两群很凶的邪灵,晚上两边打仗,连巫师都不敢从崖下的公路走。翻在这里的车也不计其数。出事多了,或者人疯得厉害,就请巫师祭祭崖神箐鬼:“祭祭嘛好一段,不祭嘛又发(发病、发事)。”
人为的放蛊施咒,也会引起身体失常、神经错乱。在怒江地区,最恐怖的传说之一,就是有关放蛊、杀魂、施毒咒的种种离奇案例。怒族和傈僳族乡亲告诉我们,怒江大峡谷里阴气重,蛊疾咒祸甚多。蛊是毒蛇、蛤蟆等毒虫的毒气及其他毒物混合而成的。放蛊人取芥子大一点,藏在指甲里,悄悄弹到食物中,被害人吃了必发蛊疾。传说放蛊人有蛊必放,否则会危及自身,蛊发时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在当地,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有个蛊妇某天发蛊,发不出去,蛊现形为毒蛇盘在她脖颈,要她放给自己的儿子。蛊妇无奈,只好答应。这事恰被儿媳看到,便出门密报给外出干活的丈夫。夫妻俩回来,蛊妇端出一碗蜂蜜水叫儿子喝,儿子借故要洗脸,将碗放在灶台上,烧了一锅滚水,然后掀开锅盖,突然把蜂蜜水倒进锅里,压死锅盖。只听锅里一阵炸响,蛊妇门坎都没跨出就死了。掀开锅盖一看,里面烫死了一条毒蛇。当地人说,要是她儿子喝下了蜂蜜水,不死也得疯。他们不认为这是传说,而认为是真发生过的事。他们肯定地说,直到现在,某某一带还有人养蛊(或叫“养药”),有人会“杀魂”。
据有学者在怒江地区的调查,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这里曾发生过多起因蛊事(“杀魂”或“养药”)引发的恶性杀人案件。直到1980年代,这类迷信仍很盛行。
“杀魂”,白语称“单排”,那马人称“下排”。即相信“杀魂者”(有男有女)通过对某人的简单接触,就能将他的魂摄走,或用石头压在河边,或匿藏在山林的崖石下,之后此人开始患病,甚至死亡。“杀魂”被认为是代代相传,多数是父传子,子传孙。人们孤立他们,将其撵出村寨,甚至杀害他们。
“养药”,白语称“白朵”,是类似养蛊和放蛊的巫术活动。被指为“养药者”的多是妇女,俗称“养药婆”。除白族外,本地区傈僳族、普米族和彝族群众中皆不同程度地盛行这类观念,以傈僳族最突出。传说“养药婆”多是些年轻漂亮的女子,专害小孩。凡有人体中拉出或爬出蛔虫、蛲虫一类,人们就会怀疑是某个“养药婆”施毒。“养药婆”被认为是其母所传,一般只传女不传男,而且代代相接。全县八个区都不同程度地流行“养药”的说法,并同碧江、福贡以及贡山地区傈僳族群众中的迷信活动相一致。在这类迷信观念的支配下,一些群众常说,人们对偷盗奸淫并不愤恨,却对“养药”最是痛恨,因为她们经常“毒死”人命,人们对之绝不宽容。一旦村里有人死亡,人们首先怀疑是某个“养药婆”干的,特别是从外地嫁入本地的女子,十之七八被认为是“养药”的。凡被指疑为“养药”的妇女,群众不再同她们往来,她们也不能到别人家去,红白喜事众人最忌讳她们到场,她们的女儿亦然,也没有人娶她们的女儿,女孩们只能远嫁到外地。她们时刻受人防范,暗中被监视,背后遭议论,心理上承受的社会压力是异常沉重的。
由于有关“放蛊”“养药”“杀魂”的说法太多,在怒江峡谷,“蛊疾”和“治蛊”,“杀魂”和“反咒”之类的事情,也便习以为常了。我所接触的人中,有巫者和常人,大都相信上述传说,并随口便举出很多“实例”。为了防蛊或防止被峡谷里的邪灵侵扰,人们会佩戴一些器物和饰物。传统的辟邪物是刀、弩和金玉饰品,也有与时俱进之物。
这里的人们认为,人若被蛊整着了,到医院查是查不出,治是治不好,只有请高明的祭司来解。先请卦师给中蛊人算卦,算出他中的是什么蛊,来自何方,然后请祭司“对症施法”,举行相应的祭仪(他们认为,卦师诊病、祭司治病的分工是为了公正,防止巫德不好的人为谋钱财“乱开处方”),再给病人吃半斤核桃油,加上一些漆树子,翻江倒海又吐又泻,巫、医并进,才能将蛊排出。这里的巫师和祭司很厉害,不治医院能治的病。他们宣称,有病先找医院,医院医不好的疑难绝症,才值得他们动手。
从很多经历中,我确实相信,这些怒族朋友决无以神鬼巫蛊蒙骗我们的意思。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切,而且真的会受到这些东西的伤害,或通过另外的法术得到切实的禳解。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虚妄荒诞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而且常常被他们的经验证明确实产生了作用。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已经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以一整套自足的存在方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例如,就社会组织结构而言,有放蛊施咒的蛊婆、黑巫师,也有克蛊解咒的职业化的并有分工的白巫师;在物质层面,有养蛊的秘方,也有治蛊的奇药;在符号层面,无论是口诵的咒语祭词,还是手书的符篆图贴,都具有特异的信息传递功能,对属于该文化圈的人能产生类似“信息场”的效应;与此相应的习俗、制度、观念等层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发生着作用。例如,“诊断”病因,可用竹签、草筮、蛋卜、骨占、肝决、刀卦、弓算、酒显以及观气色、看手相等方式获知信息;治病救人,则视不同病因,用素祭、血祀、咒语、祝词、歌舞以及成套的象征仪式和活动来禳灾除病。他们似乎生活在某种特定的人天关系中,在这里,人疾与具体到一阵雾霭、一堆山土的天象地气,命相与穿什么颜色衣服便产生什么生克关系的阴阳五行,都可神秘地互相感应。
这些以不同形式体现的器物、符号、观念、制度、社会组织等文化因素,构成一个影响力极大的文化系统。长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能不受到它潜移默化的影响。那种无形而又真实的处境,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你能体验得到的氛围,是很难用数据等来量化表述的。事实上,在人类学界,有许多国际知名的例证一再说明,人的文化处境或精神氛围,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如非洲某些部落的“骨指器”或巫师的咒语,足以让一个强壮的部落成员因极度恐惧而丧命,因为他在多年强烈的文化或精神暗示中,已经认同了这样的“事实”——一旦被魔骨所指或被巫师所咒,必死无疑。这种情况或许正如传闻里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一个死刑犯被告知他将被放血处死,然后他被蒙上双眼,在他静脉处用刀背假作切割,放水滴流,造成流血的效果,不一会儿,那犯人果然死了,死于心律衰竭。
在怒江大峡谷,每当夜暗星密时,天被石崖巨大的怪影挤成一条无头无尾的长虫,江涛啸声和巫师奇异喉音的混响,若有若无地直透心骨,这时候,我便有些体会到这峡谷里所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的意义了。只要峡谷还是这样,峡谷人所接受的文化暗示和心理暗示还是这样,神话和巫术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精神需要。这不是用简单的“唯物”“唯心”一类的词,可以界说的。俗话说“信则灵”,这或许应从一种跨文化精神病学的角度去理解。在我们的考察中,还了解到这样一些例子:同在怒江峡谷中生活,改信基督教的本地民族,传统的神话和巫术对他们影响便较少,甚至不再产生作用,巫蛊之疫也随之减少。我也曾想见见信巫蛊者谈之色变的鬼怪邪灵,甚至在夜晚独自走过那个传说中弄疯、弄死不少人的山箐,虽然脊背发麻,但我还是关了手电,拿出自动相机,准备真碰到个鬼怪时能抢到个镜头——我当然一无所见。这是否说明,只有置身(实际是置心)于特定的文化处境中,对其千百年传承的集体意识和文化暗示进行认同,那种“感应”才会发生?而对于不在其文化处境中的异文化介入者或改变了信仰的当地人,传统的“暗示”便不再具有作用?如果是这样,像巫蛊所致的“病”,便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去理解。当然,巫蛊术不纯粹只是一种心理行为。事实证明,即使是原始时代的巫师,在药物等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惊人的,例如毒蘑菇、仙人掌碱等致幻剂的使用。因为原始巫术往往是巫—医、巫—技合一的。也就是说,巫蛊的文化或精神场景,也有一定的物质或技术的依托。
我们的考察,或许就应该从这样的时间跨度和学科跨度基础上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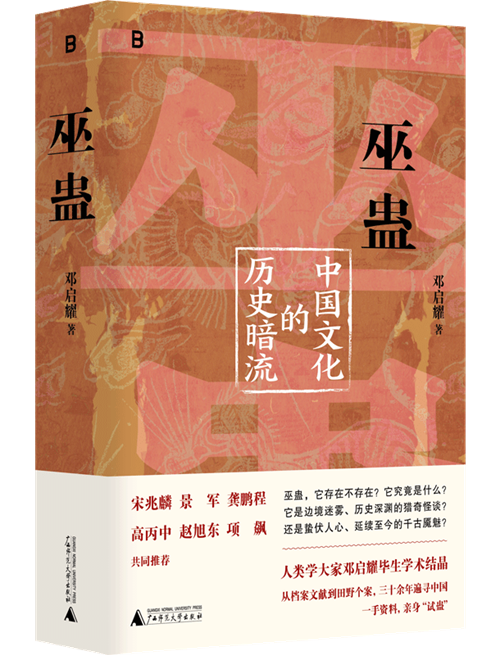
《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邓启耀著,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
 轻舞信息网
轻舞信息网







